
我有个朋友,特别爱批评欧洲历史,说欧洲的古代文明史全是假的,只有中华文明史是有据可查的。
我笑着问他:“你家有几本民国时候的书?”
他说一本都没有。
我又问:“你家有几本清朝时候的书?”
他直摇头,民国的书都没有,怎么可能有清朝的书。
于是,我对他讲:“与历史几千年相较,最近一百多年,是人类保存物品最容易的时代,而在这个时代,且你还是个读书人,家里连百把年的书籍都没有留下,你能要求过去几千年能留下多少东西?”
他不服,反问我:“私家不留,朝廷不会留吗?”
不是说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史官,但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残暴的屠戮,除了故宫,你能看到几间其它像点样子的历代宫廷建筑?根基不保,何况书矣?!如果算上断断续续的数百年大分裂和北方民族频繁制造的祸乱,不要往太远处究,南宋以前的真迹,能留下的就寥寥可数,落难的王侯不如奴,一把刀结束前王的命,一把火烧掉前王的城,这不就是中国历史吗?
胡适曾经讲过一句话:“中国人作史,最不讲究史料,神话官书,都可作史料,全不问史料是否可靠。”
他还说过:“诸子之书,无两家相类者,糊涂混乱,说者纷纷。”
很有趣的是,胡适一边是不信中国史书,一边又用一年的时间爬进史书堆里编成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被当时和后来的人吹捧得一塌糊涂。
为什么就没人反问一下:“胡适先生的书里引用了数百本史籍,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甄别如此庞大史料的可靠性?“
历史这个东西,大家不要老说欧洲史不可信,若较真,哪国的古史都不那么可信,咱中国人今天阅读的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,绝无可能是原作者的手稿本,不知道经过了历朝历代多少文人的杜撰与篡改,将就着用也还差不多,有那么一成真实就算是“真史“了。《三坟》,《五典》,都只是传说,带神的故事,不那么像是历史。
不要固执地认为历史不是小媳妇,在我看来,历史就是小媳妇,你没办法不让她尽量更美,因为你决定不了历代史学化妆师的行为,过去如此,今天和今后皆如此。
还是说历史,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大部分残破的古城墙被拆了,时至今日,还有许多人在传播一个结论:“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伟大的,他们坚持保留古城墙,而郭沫若是有罪的,因为他建议拆除旧城墙。“
如果不加思索,很容易认可这个结论。
然而,真是这样吗?不是。
城墙,是干嘛用的?不就是冷兵器时代用来抗敌的吗?热兵器时代到了,你留着它何用?供后人旅游参观?也许可以,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中国还有不少城市留下了古城墙,但并没有人把到某地去看旧城墙当作网红打卡点炒作。
法国巴黎的梯也尔城墙长达33公里,比北京城墙长得多,上世纪也被一次性全拆,法国人并没讲多少婉转的理由,更没有骂拆墙者,他们很直接地就讲影响了巴黎城市交通规划,环城交通线重于古城墙。
人啊,有时候用个“古“心包住一些所谓的历史虚荣感,其实是一种恋旧心态,真想看墙,长城那么长,比北京城的那些残破旧墙要好看得多,去看便是,没人提出过要拆它。
如果没有”托古改制“的政治偏好,完全没必要以”古“之名给人定功过,如果郭沫若建议把故宫拆了,那便真有罪,因为宫里有人性与奴性的历史见证。
现在,中国流行着“文博热“,年轻人也爱,真爱假爱不知道,人流量爆棚是真实的。
博物馆是个什么地方?在我眼里,它跟和尚庙、尼姑庵和道观都是一样的存在,把旧的东西搁在一起,学外国人取个古代没有的名字叫博物馆,然后就高大上了一些。
寺庙与道观,不也是越古的地方越出名吗?越古的地方就越“有文化“。在欧洲的教堂里,也藏着丰富的古物,甚至欧洲的古代史都是出于教堂,在这一点上,它跟中国是相通的。撇开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区别,和尚,尼姑,道士,跟博物馆的人员干的是同一种事。人流量,并不见得反映信仰真实度,文博热和叩头热的真诚指数相差无几。
如果你不是真爱与真信,建议少凑点热闹,把空间留给信徒就是修身养性。
近几十年,对于外国人,咱们的脑子也受了许多蒙蔽,下面就简单开几个脑孔。
公知们曾讲:“资本主义国家是藏富于民,政府穷,人民富,中国是反着的,人民穷,政府富。“
因为我没在外国生活过,以前不怎么敢评这个结论。
新冠疫情倒是帮了我,咱中国又封又检地搞了三年,老百姓虽受了些影响,但基本生活也算正常。美国人三个月都挺不住,为了保证底层人生活,特朗普给他们发了三次钱,部分州还额外发了生活补贴。我看了一档日本东京电视台录制的节目叫《可以跟着你回家吗?》,采访的都是中底层百姓,发现许多日本家庭疫情期间跌入贫困深渊,没看出他们家底很厚实。
资本主义国家藏富于民到底藏在哪里?存款?金银珠宝?藏着不愿拿出来用?美国的33万亿美元国债得摊到国民身上,算藏富吗?
发达国家的富是真的,但“藏富于民“可能不是真的,“藏富于富人”才是真的,要不,财富去哪儿了呢?
以前,公知说资本主义国家崇尚契约精神,有人真信了。
过去不怎么信,现在更不信。美国的总统,可以近似看成是世界总统,按理讲,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代表,即使现在有很多同盟国家对他不满,但还是愿意跟着他走,他理当成为契约精神的标准执行者。然而,他没有,契约在他手上的变化比翻书还快,精神是确定不在了。
契约,里面永远藏着一个“强弱”分别,守不守看强弱变化。
我暗地里寻思,以前,为啥就那多人相信鬼话?其实很简单,过去,西方国家的政客藏得深、做得精,碰到特朗普这个不善矫作的便全露馅了,他不只是脱了自己的裤子,把整个西方的裤子一起给脱了,甚至把中国公知的裤子也顺带给脱了,搞得他们现在连撒谎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
还有个事得拿出来说说,中国文化界的文学、影视、走秀等作品到欧美去评奖,欧美评委经常会给一些不美又不好的中国人和中国作品颁个特大奖,搞得中国很多人心里不舒服。
这时候,中国公知又上场了,他们说:“不要玻璃心,那只是文化差异,那只是审美差异,无关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。“
这个说法,我一直是不信的,但很多人相信,并且还老是喜欢拿“文化差异“来教育别人。
有什么法子反击呢?很简单啊!让他们多看些欧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,欧美影视剧中的男女主角在中国人眼里也都是绝顶的美女帅哥啊!跟中国人的审美观也都是统一的啊!没看到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欧美主角长得歪牙眯眼,也没看到欧美名利场中混得风声水起的都是怪异形状。
有些人,你用不着信他们,想骗你,有时候用“文化差异“,有时候又用”文化无国界“,怎么好骗就用哪招,多换边脑子想事,你就不会被骗了。
人有时候得装点糊涂,但又不能真糊涂,偶尔换边脑子想问题可以让自己从惯性思维里解脱出来,形成一种可以属于自己的非惯性思维。
比如说审美,每到银杏叶黄的时候,几百米的泥巴路两旁挤满了打卡人。为何?因为她们都在狂热于“金黄“的美。岳麓山枫叶红的时候,景象也是一样的,因为都爱那个”红“。
红,黄,比绿更美吗?不,它们是等美的。
如果全世界植物的主体颜色是黄色或红色,那绿便被打卡了,它们不是美的区别,是人对多寡的疲劳度不一样。
榛子,一种坚果,产于北方,南方人吃得少,偶尔吃一次,觉得味道不错。
吃了几次之后,我就问自己:“如果直到今天才第一次吃上花生,而榛子连续吃了几十年,会不会觉得花生比榛子更好吃?“
再比如说做人哲学,“动机“是思维惯性,多数人爱表明一种态度,通常有”动机“放在心里,随处可听的话术有:我不在乎钱,我是直性子,我不喜欢拍马屁,我从不在背后讲人闲话,我从不干缺德事,我对当官没有兴趣,等等。
人为什么爱“表明“这些高尚的态度?动机自然是想让人高看他。
然而,不妨反问一下:那钱都有谁在在乎它?马屁都是谁拍的?闲话你没讲过那都是谁在讲?都对当官没兴趣,那么多官都是谁给占了?
事实上,全体国人都爱上这个“不“字,从文化根源上追溯,其实是受老子”不争主义“的深刻影响,总希望把自己置于不与人争的无害状态,以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。
不过,人,自从由动物变成了人,那便开始了争,不争,就不能好好地活,争不下去,那是结果,不是动机,真到了不争的时候,就完全不需要说那个“不“字了。
近几个月,美国挑起了跟中国的对抗,有位教授说:“美国估计要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,为什么我们老是被孤立?为什么不像别国一样找它谈?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有多困难?“
我不想揣测他的本意,只是回应:“你可以反过来想想,美国单斗中国若有把握,它还需要联合狗友吗?想拉帮结派,说明它还是畏惧中国,以一敌众咱又不是没打过,内心真怕了它,一对一都打不过它。“
人的大脑,从小到大一直被漂洗和刻画,图像基本都是别人的。
进入社会后,每一步都在积累生活素材,如果可以,到了适当的年龄,不妨在大脑的另一侧留下自己对世界认知的自画像。
附言:
1.中日友好医院的肖某带出了协和医院的种种事情,接着还让许多单位躺枪。评:很快会被忘记,这些都不算事,因为看不见事的人见事就大,而那些操作事的人心中就没啥大事。有很多网友留言让我讲这事,但我本人对所谓的真相也已经没兴趣了,其实也是不能深讲,任他们玩吧!
2.美方希望与中国谈起来,中国商务部回应正在评估。评:谈出结果,可以接受妥协的空间,强加的结果,就没有可接受的余地。
3.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出台。评:不管公还是私,都按照一个平等法律就好,依法是最好的营商环境,进不进得看企业自己。
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!祝大家都有劳动的机会!
写于2025年5月2日星期五
【文/孙锡良,红歌会网专栏学者,独立时评人。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“孙锡良B”】






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 头条焦点
头条焦点



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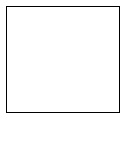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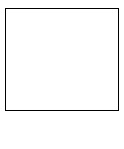

【查看完整讨论话题】 | 【用户登录】 | 【用户注册】